达摩流浪者 | 杰克·凯鲁亚克
文章类别:
- 9月 20, 2022
- 1 条评论

 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
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你必须注册后才能投票!
快捷索引
杰克·凯鲁亚克
BOOKS51.COM 祝您开卷有益,如果你真喜欢这本书,请购买正版!
注册后直接可见福利:
百度网盘资源:
感谢ibooks.org.cn[读书小站]分享资源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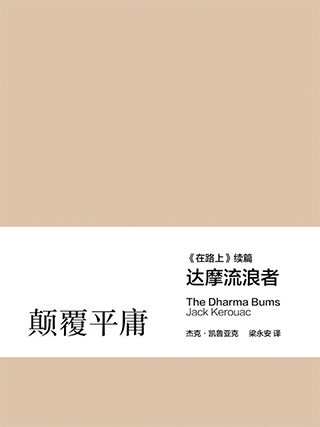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关于背包革命、自然精神、生命思索以及禅之道的小说,讲述的是1955年两个热情洋溢的青年贾菲与雷蒙追求真理以及禅理的故事。他们以其特殊的世界观追寻着生命的直觉、纯净与唯美,马拉松式的狂欢与旧金山的纵情“雅雍”无疑是自由的最佳注解,而诗人的情怀与托钵僧的苦旅,历经马特峰与孤凉峰的超拔洗涤,让尘世显得如此澄透。《在路上》出版之后的一年,凯鲁亚克将《达摩流浪者》献给了寒山子,并于美国西海岸勾勒出禅疯子与登山背包行者的朝圣路线,也为“垮掉的一代”确立了的文学版图,平添些许东方色彩。
作者简介
杰克·凯鲁亚克(Jack Kerouac,1922-1969),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,凯鲁亚克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,父母为法裔美国人,他是家中幼子。他曾在当地天主教和公立学校就读,以橄榄球奖学金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,结识爱伦·金斯堡、威廉·巴勒斯和尼尔·卡萨迪等“垮掉的一代”。
凯鲁亚克大学二年级退学从事文学创作,并辗转于美国海军和商用航运公司等处。一九五○年,第一部小说《乡镇和城市》出版。一九五七年的《在路上》问世后,他成为“垮掉的一代”的代言人,跻身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著名作家行列。他还著有《达摩流浪者》、《地下人》、《孤独的旅人》和《孤独天使》等作品。
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,凯鲁亚克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去世,享年四十七岁。
内容节选:
我生平所遇的第一个”达摩流浪者”就是上述的小老头,而第二个则是贾菲·赖德–他是” 达摩流浪者”的第一名,而且事实上,”达摩流浪者”这个词儿,就是他始创的。贾菲来自俄勒冈,自小与父母和姊姊住在俄勒冈东部森林的一闾小木屋。他当过伐木工和农夫,热爱动物和印第安人的传说,这种兴趣,成为他日后在大学里研究人类学和印第安神话学的雄厚本钱。后来,他又学了中文和日文,成了一名东方学家,并认识了”达摩流浪者”中的佼佼者–中国和门本的禅师。与此同时,身为一个在西北部长大、深具理想主义的青年,他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那种老式的无政府主义。又有很深的认同。他懂得弹吉他,喜欢唱老工人和印第安人的歌曲。我第一次看到他,是在旧金山的街头。(我忘了提,离开圣巴巴拉之后,我靠着一趟顺风车一路坐到旧金山。说来难以置信的是,载我的人是个年轻的金发美女,她穿著件无肩带的泳衣,赤着脚,一个脚踝上戴着金镯子,开的是最新款的肉桂色林肯牌”水星”轿车。她告诉我,她很希望有安非他命提神,让她可以一路开车开到旧金山,而凑巧我的圆筒形行李袋里就放着些安非他命。)我碰到贾菲的时候,他正踩着登山者那种奇怪大步在走路,背上背着个小背包,里面放着书本、牙刷之类的东西。这是他入城用的背包,有别于他的另一个大背包–里面装的是睡袋、尼龙披风、炊具和所有爬山时用得着的东西。他下巴蓄着一把小山羊胡,因为有一双眼角上斜的绿眼睛,让他很有东方人的味道,但他完全不像波西米亚人,而且生活得一点不像吊儿郎当、绕着艺术团团转的波西米亚人。他精瘦、皮肤晒得棕黑、活力十足、坦率开放,见到谁都会快活说上两句话,甚至连街头上碰到的流浪汉,他都会打个招呼。而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,他都会搜索枯肠去思索,而且总是进出一个精彩绝伦的回答。
“咦,你也认识雷蒙·史密斯?你是在哪认识他的?”当我们走进”好地方”酒吧的时候,大伙食问他。”好地方”是北湾区的爵士乐迷喜欢聚集的地方。
“我经常都会在街上碰到我的菩萨!”他喊着回答说,然后点了啤酒。
那是个不同凡响的夜,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夜。当天晚上,贾菲和一些其它的诗人预定要在六号画廊举行一个诗歌朗诵会(对,贾菲也是诗人,而且会把中国和日本的诗译成英文),所以相约在酒吧里碰面,人人都显得情绪昂扬。不过在这一票或站或坐的诗人当中,贾菲是唯一不像诗人的一个(虽然他是个如假包换的诗人)。其它的诗人,有像艾瓦·古德保那样一头蓬乱黑发的知识分子型诗人,有像奥沙伊那样纤细、苍白、英俊的诗人,有像达帕维亚那样仿佛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,不食人间烟火的诗人,有像卡索埃特那样打着蝴蝶领结、一头乱发的死硬派无政府主义诗人,也有像沃伦·库格林那样戴眼镜、文静、肥得像大冬瓜的诗人。还有其它有潜力的诗人站在四周,而他们所穿的衣服虽然形形色色,但共同的特征是袖口已经散线和鞋头已经磨损。反观贾菲,穿的却是耐穿耐磨的工人服装,那是他从”善心人”-类的旧衣商店买来的二手货。这身服装,也是他登山或远足时穿的。事实上,在他的小背包里,还放着一顶逗趣可爱的绿色登山帽,每当他去到一座几千英尺高的高山下,就会把这帽子拿出来戴上。他身上的衣服虽然都是便宜货,但脚上穿的,却是一双昂贵的意大利登山靴。那是他的快乐和骄傲,每当他穿著这双登山靴昂首阔步踩在酒吧的木屑地板上时,都会让人联想起旧时代的伐木工。贾菲个子并不高,身高只有大约五英尺七英寸,但却相当强壮、精瘦结实、行动迅速和孔武有力。他双颧高凸,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,就家一个正在咯咯笑的中国老和尚的眼睛。而他颚下的小山羊胡,抵消了他英俊脸庞的严峻。他的牙齿有一点点黄,那是他早期森林岁月不注重口腔卫生的结果,但他并不以为意,笑的时候总是把嘴巴张得大大。有时候,他会无缘无故突然安静下来,忧郁地看着地板,仿佛心事重重。不过,他还是以快活的时候居多。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的投契,对我所谈到的事情–像关于小老头流浪汉的,有关我坐免费火车或顺风车旅行的体验的–都听得津津有味。他有一次说我是个”菩萨”(”菩萨”的意思约略相当于”大智者”或”有大智能的天使”),又说我用我的真挚妆点了这个世界。我们心仪的佛教圣者是同一个:观世音菩萨。贾菲对西藏佛教、中国佛教、大乘佛教、小乘佛教、日本佛教,乃至于缅甸佛教,从里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但我对佛教的神话学、名相以至于不同亚洲国家的佛教之间的差异,都兴趣缺缺。我唯一感兴趣只有释迦牟尼所说的”四圣道”的第一条(”所有生命皆苦”),并连带对它的第三条(”苦是可以灭除的”)产生多少兴趣,只不过,我不太相信苦是可以灭除的。尽管《楞伽经》说过世界上除了心以外,别无所有,因此没有事情–包括苦的灭除–是不可能的。但这一点我迄今未能消化。
前面提到的沃伦·库格林是贾菲的死党,是个一百八十磅的好心肠大肉球,不过,贾菲却私底下告诉我,库格林可不只我肉眼看到的那么多。
“他是谁?”
“我的老朋友,打从我在俄勒冈念大学的时代就认识的死党。乍看之下,你会以为他是个迟钝笨拙的人,而事实上,他是颗闪闪发亮的钻石。你以后会明白的。小觑他的话,你准会落得体无完肤。他只要随便说句话,就可以让你的脑袋飞出去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菩萨,我认为说不定就是大乘学者无着⑩的化身转世。”
“那我是谁?”
“这个我倒不知道。不过也许你是山羊。”
“山羊?”
“也许你是穆德菲斯。”
“谁是穆德菲斯?”
“穆德菲斯就是你的山羊脸上的泥巴。如果有人问你’狗有佛性吗?’,那你除了能’汪汪’叫两声以外,还能说些什么呢?”
“我觉得那只是禅宗的猾头话。”我这话让贾菲有点侧目。
“听着,贾菲,”我说,”我可不是个禅宗的佛教徒,而是个严肃的佛教徒,是个充满梦想的小乘信徒,对大乘佛教感到望而生畏。”我不喜欢禅宗,是因为我认为禅宗并没有强调慈悲的重要性,只懂得搞一些智力的把戏。”那些老禅师老是把弟子摔到泥巴里去,只是因为他们根本答不出弟子的问题,”我说,”我觉得这很卑鄙。”老兄,你错了。他们只是想让弟子明白,泥巴比语言更真实吧了。”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复述贾菲那些精彩的回答,但他每一个见解,都让我有被针扎了一下的感觉,到后来,他甚至把一些什么植入了我的水晶脑袋,让我的人生计划为之有了改变。
那个晚上,我跟着贾菲一票嚎叫诗人前往六号画廊,参加诗歌朗诵会。这个朗诵会的其中一个重要成果,就是带来了旧金山诗歌的文艺复兴”。每个我们认识的人都在那里。那是一个疯到了最高点的晚上。而我则扮演了加温者的角色:我向站在会场四周那些看来相当拘谨的听众,每人募来一毛几角,跑出去买了三瓶大加仑装的加州勃根地回来,然后对他们频频劝酒,因此,到十一点轮到艾瓦·古德保登场,嚎叫他的诗歌〈嚎叫〉时,台下的每个人都像身在爵士乐即兴演奏会那样,不断大喊”再来!再来!再来!”,而俨如旧金山诗歌之父的卡索埃特,则高兴激动得在一旁拭泪。贾菲朗诵的第一首诗,是以丛林狼为主题(就我的浅薄知识所知,丛林狼是北美高原印第安人的神只,不然就是西北部印第安人的神只)。”‘操你的!’丛林狼喊道,然后跑走了!”贾菲对着口下一群杰出的听众念道,让他们高兴得嚎叫起来。真是神奇,明明是”操”这样粗俗的一个字,被他放在诗中,竟显得出奇的纯净。他其它诗歌,有一些是能反映他对动物的爱的抒情诗行(如写熊吃浆果的一首),有一些是能显示他渊博的东方知识的神秘诗行(如他写蒙古的犁牛的一首)。他对东方的历史文化的了解深入到什么程度,从他写玄奘的一首就可见一二(玄奘是个中国的高僧,曾经手持一炷香,从中国出发,途经兰州、喀什和蒙古,一路徒步走到西藏)。至于贾菲一贯秉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,则表现在一首指陈美国人不懂得怎样生活的诗歌里。而在另一首描绘上班族可怜兮兮生活的诗,则流露出他曾在北方当伐木工的背景(他在诗中提到现在的上班族,都被困在由链锯锯断的树木所盖成的起居室里)。他的声音深沉、嘹亮而无畏,就像旧时代的美国英雄和演说家。我喜欢他的诗所流露出的诚挚、刚健和乐观,至于其它诗人的诗,我觉得不是失诸太耽美就是太犬儒,要不就是太抽象和太自我,或是太政治,又或是像库格林的诗那样,晦涩得鸡以理解(他诗中提到的”厘不清的过程”这词儿倒是很适用于形容他的诗)。不过,当库格林的诗说到了悟是一种很个人性的体验时,我注意到其中具有强烈的佛教和理想主义的色彩,跟贾菲很相似,而我猜得到,那是他和贾菲在念大学的死党时代所共享的(就像我和艾瓦在东部念大学时也共享过相同的思想理念一样)。
书廊里一共有几十人,三五成群地站在幽暗的台卡,全神贯注地聆听朗诵,唯恐会漏掉一个字。我在一群群人之间游走(面向着他们而背对着舞台),去给每一个人劝酒,有时,我也会坐到舞台的右边,聆听朗诵,不时喊一声”哇噻”或”好”,或说上一句评论的话(虽然没有人请我这样做,但也没有人提出反对)。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夜。轮到纤细的达帕维亚上场时,他拿着一迭像洋葱皮一样纤细的黄色纸张,用细长白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翻,一页一页地念。诗都是他的亡友奥尔特曼所写。奥尔特曼前不久才在墨西哥的济华花过世,死因据说是服用了过量的佩奥特碱(一说是死于小儿麻痹症,但这没什么差)。达帕维亚没有念一首自己的诗–这个做法,本身便够得上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挽歌,足以在《堂吉诃德》的第七章里挤出泪水来。另一方面,他念诗时所使用的纤细英国腔调,却让我不由得在肚子里大笑起来。不过,稍后和他熟谙以后,我发现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。
会场的其中一个听众是罗丝·布坎南。她有着一头红短发,是个骨感的美女,跟谁都能发展出一段罗曼史。她是个画家模特儿,也写写作。当时的她,正跟我的死党寇迪打得火热,所以显得神采飞扬。”怎么样,罗丝,今晚很棒吧?”我喊道,而她则拿起我的酒瓶,仰头喝了一大口,眼睛闪闪有光地看着我。寇迪就站在她背后,两手揽住她的腰。今天晚上当主持人的是卡索埃特,他打着个蝴蝶领结,穿著件破破烂烂的西装。每当一个诗人朗诵过后,他就会走上台,用他一贯的逗趣刻薄语气,说一小段逗趣的话,介绍下一位朗诵者。所有诗歌在十一点半朗诵完毕,在场的听众都议论纷纷,很好奇这个朗诵会将会对美国诗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,而卡索埃特则如上面提到过的,激动得用手帕拭泪。接下来,一票诗人分乘几辆汽车,一起到唐人街,在其中一家中国餐馆里大肆庆祝叫嚣一番。我们去的”南园”餐馆,凑巧是贾菲的最爱。他教我该怎样点菜和怎样使用筷子,又说了很多东方禅疯子的趣闻轶事给我听。这一切,再加上桌上的一瓶葡萄酒,让我乐得无以复加,最后甚至跑到厨房的门边,问里面的老厨子:”为什么达摩祖师会想到要向东传法?”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他眨了一眨眼睛回答说。我把这件事告诉贾菲,他说:”好答案,好得无与伦比。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心目中的禅是怎么回事了。” 贾菲还有其它好些值得我学习的东西,特别是怎样泡妞。他那种无与伦比的泡妞禅道,我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就见识到。
文章类别:
本文链接: http://www.books51.com/14830.html
【点击下方链接,复制 & 分享文章网址】
达摩流浪者 | 杰克·凯鲁亚克 → http://www.books51.com/14830.html |
上一篇: 大中华文库・浮生六记(汉英对照 )
下一篇: 十杆枪 | 克里斯·凯尔, 威廉·道尔

 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
(0 次顶, 0 人已投票)你必须注册后才能投票!






禅和背包族革命
在1963年4月23日的《纽约时报》上,有个叫乔治.普林顿的人写了篇名为《所有病态的水手》的评论。在这篇简短的评论里,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有几位作家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美国流浪汉小说。包括写了《奥吉.马奇历险记》的索尔.贝娄,写了《第22条军规》的约瑟夫.海勒,当然还包括《在路上》的作者杰克.凯鲁亚克。
这类小说一般都很冗长,充满了怪人、离经叛道者和荒诞的角色。情节有一连串冒险事迹构成,围绕着主角发展。小说中往往由一个追寻的目标或者理念,让人物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。杰克.凯鲁亚克的另一部小说《达摩流浪者》便是这一种小说的典型标本。这是一本流水帐式的游记,没有高潮、悬念,没有详与略,重点与次要之分。正如贾菲论述雷的写作时提到的那样,完全是自动式的写作。人物中的雷和贾菲都是脱离于社会标准的禅疯子,行为放荡不羁,不受拘束。更重要的是,在雷的不断流浪中同样也包含着一个理念和追求。
这是一部献给中国古代的诗人寒山子的小说。在20世纪50至70年代,寒山子曾经影响了一代美国的年轻人。比如小说中的贾菲和雷,如果你将这部小说看成是自传式的,也可以说是现实中的杰克.凯鲁亚克和诗人加里.斯耐德。在他们的想象中,寒山子是一位厌弃了城市和这个世界躲到深山隐居的禅疯子,是将自身从社会文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、寻求原始的真性情的人。这种行径和他诗中透露出的禅意契合他们的行为和欲求。于是,寒山子的禅也就成了他们的理念和追求。他们模拟寒山子的生活方式,自动远离美国的工业文明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,搭便车流浪于各个城市之间;或是登到高山之巅,寻求这个世界的真理和自我灵魂的净化;或是在树下、玫瑰花丛间打坐、祈祷,进行着他们认为是这个世界上仅剩的高贵活动。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过都是“空和觉”;他们感应到万事万物的脉搏,感到自己已经获得了拯救。在小说的结尾,雷按照贾菲的指引来到了孤凉峰,在那里居住了两个月。两个月后,当他要重新回到城市时,他感到自己长大了。他学会了感恩,领悟到“不管是小孩还是无知的人,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对待。”上帝应该赐福给所有的人。此时此刻,雷几近获得了完美的“神爱世人”的博大胸襟。
由于时空的差异,雷的“禅”在我们看来有时会显得矫揉造作。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这本书所要传达的最动人的信息。“禅”或许只是个幌子。他们打着这个幌子,实践了一种他们所要追求的生活方式。这种方式带着反抗、决绝,带着青春的激情和放荡,以及难得的清醒。而他们所要与之决裂的是当时主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。
在这种生活方式里,“现代人为了买得起冰箱、电视、汽车和其他她们并不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,让自己监禁在一个工作-生产-消费-工作-生产-消费的系统里”。正如雷的一首诗中所描绘的,他们是在“旷野中疲于奔命的老鼠”。他们住在高级的房子里,在同一个时间里看着相同的电视节目,以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着事情。他们是被机械文明规训和奴役的人。
“达摩流浪者”在全世界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考的时候,需要一种理念支撑他们,才能用他们沾满尘垢的嘴唇放声大笑。不管这种理念是东方的禅还是西方的基督,关键是他们是对此真诚的,是信仰的,他们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虚妄。他们借助“禅”到达了世界的另一端,规避了被现代文明驯化的命运。
贾菲在书中说,他有一个美丽的愿望,他期待一场伟大的背包族革命的诞生。到了那时候,将会有无数的年轻人,背着背包,在全国各地流浪。他们会爬上高山去祈祷,会逗小孩子开心,会取悦老人家,会让女孩子爽快。他们会写着突发奇想、莫名奇妙的诗歌,会把永恒自由的意向带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灵。
正是背包族革命的图景,以及他们对这种图景的实践,而不是有关“禅”的理念才是小说中最动人的。而对于那些生活在都市中、在朝九晚五式的生活里平庸地消耗青春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。